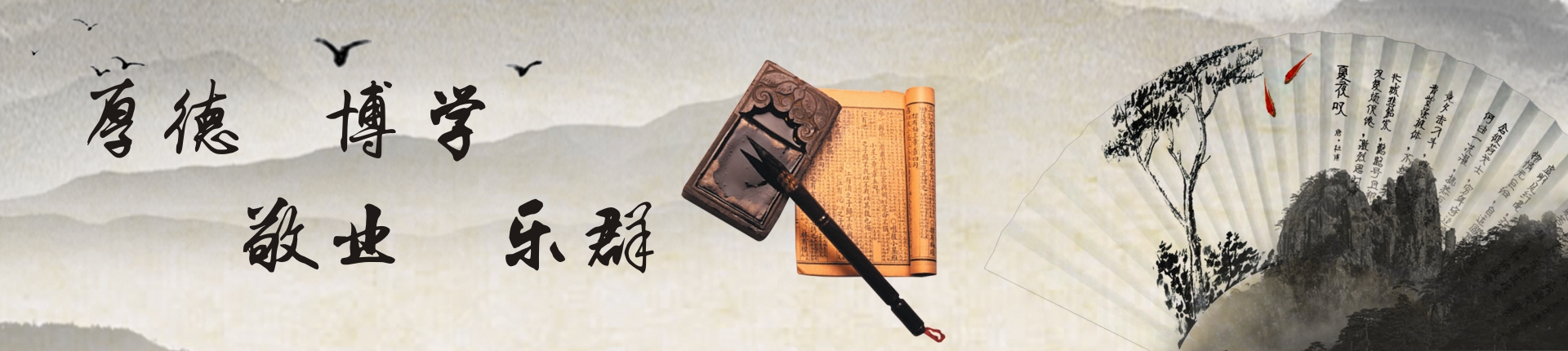朴 窑
许久未归,而今再忆故园,却发现那方小小的窑屋只存在于心中。
外公与外婆对于“家”的记忆并不是后来重建的瓷瓦砖石堆彻的平屋,而是外公亲手搭建的土窑。外婆常忆到她与外公在新窑的那段日子,外公是铁道兵,年轻时也曾为新疆的道路建设作出贡献,兵役结束回村后,便邀了兄弟几个合伙搭建,因为性格要强,即便被炎炎的夏日晒的睁不开眼,但仍执意自己修筑。
每每此刻,外婆的面庞总会拂过一抹笑意,微飕送馨 ,被岁月的痕迹侵蚀的面容上总是洋溢着幸福,外公因疾病只得坐卧在轮椅上,当看着外婆笑嫣时,便也会陪着外婆一起享受时光,初日生艳,他们背后的土窑在微光之下格外耀眼,那方小土窑,是独属外公外婆的幸福。
母亲与舅舅对“家”的记忆也便是那方小土窑,母亲胆小,每到夜晚总会因梦魇而不得入眠,彼时外婆便会在蝉鸣四起的夏夜轻抚母亲的幼小身躯,但舅舅总会在这样的夜晚睡得格外安稳,外公也早已在家人围伴的土坑上安然入梦。而今再当母亲回忆时,她说,这才是幸福原本样子。躁热,蝉鸣的夏夜星空之下,这方小土窑,是母亲心中最完美的幸福。
我对于这小窑的记忆是在我五岁之前,我是被外公外婆一起带大的,不过,我从没住进小土窑。我记事时,我们便已搬进院东新修的平屋了,小时候总爱与舅舅家的蕊蕊妹妹跑进窑中探险,时不时捡些古旧但对我们来说新奇的玩意,顾不上沾满泥土的脏手,也顾不上被太阳晒得黝黑发红的面颊。儿时的快乐很简单,一块生锈的铁皮青蛙玩具,便足矣占据我全部的内心.......
后来的年华好似如风吹落树叶那般飘逝,许久因学业繁忙不归的朴院,再见到时,那方小土窑前立了一根木桩,不知何时已被贴上“危房”的标签,外婆再也不许我们靠近了,她总会说,“窑会塌的,不敢进去”,我很听话,便再也未靠近那方小土窑。
回头间,外公倚着拐杖,他看着小土窑,看着外婆,只能勉强挤出一个笑容。我并不知道,此时外公已病入膏肓,直至外公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之时,我想要伸手抚碰外公的面庞,母亲拦着我,让我回去吧,我奋力去用手抓住病床:“外公,下次见”我嘶吼着,但我仍很听话,我当然回去了。可出了病房,扭头那一瞬,我恍惚间看到外婆掩面低应,这才醒悟,那一别,竟是永别。
随着外公的离世,小土窑也塌陷了,外婆看着塌陷的废墟发呆,那时候的外婆无助的好像一个失去庇护的孩子,任凭泪水模糊了双眼......
我,不知所措,母亲与舅舅从低声抽泣逐渐变成嚎啕大哭......外公走了,原先小土窑的位置被重新修筑的两层平屋所替代,但那里从没住过人,从来只是放置着外公的灵堂与外公在时的旧物。
故日朴窑已不在,故日之旧人亦离别,而那方土窑也已消逝于世、深埋于心,每当忆起,便也一同念着故人......
作者简介
苏祺媛,人文学院汉语国际教育242班的学生,兴趣广泛,热爱观察生活与文学创作,爱好钢琴弹奏,文章曾在县级《桥山》杂志中刊登多期。